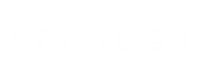本篇文章1741字,读完约4分钟
一连几天,上海的雨连绵不断,看着窗外下雨的街道,小克勒总会想起戴望舒的《雨巷》。
上海就是标准的江南雨天,细细密密的雨滴打在伞上似乎没什么重量,却总能轻轻柔柔地沾湿最外面的衣服,就像给行人附上一层丁香一样的淡淡愁怨,也把匆匆的城市染成一条悠长的雨巷。
这样一想,越发觉得这个天气读戴望舒的诗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除了应景的《雨巷》,小克勒还很喜欢戴望舒的另一首诗《有赠》,这是他为自己相恋8年的初恋女友而写,诗的最后写道:“终日我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在戴望舒因为自己再度失恋而写下这首情诗后不久,当时正在为电影《初恋》作曲的“歌仙”陈歌辛由此受到了启发,当即决策把《有赠》谱成了电影主题歌。
这部电影是通过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两位女性的爱情纠葛而展开的,所以陈歌辛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自己的文友、与影片的男主人公有着同样命运、同时同样是诗人的戴望舒。
陈歌辛
戴望舒
后来,陈歌辛在戴望舒的原诗前加上了自己诗句:“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呀,你在何处......”,谱成了那首惆怅无奈却又深情潇洒的情歌《初恋女》。
不过,“歌仙”的灵感来源可不仅仅是戴望舒的爱恨纠葛~被人问到为什么自己的大名要用“辛”这个字时,陈歌辛说:“我的歌曲是师法劳动号子与民歌,因为此不能数典忘祖,我们必需为辛劳的大众而歌。”
说起民歌,你也许想到陕北的信天游、广西的“刘三姐”、云南的“阿诗玛”……北方的粗旷、南方的多情,偏隅之地交通不十分便利,于是有了各种调子迂回于山间,以南腔北调往来传播着当地人的深情厚意。
可是上海民歌常常会被忽略——身处平原的上海无山可喊,又时常带着洋派妆容,不少人便以为沪上缺乏众多媒体转载的民间歌曲,其实不然。
八拼档杠棒号子
早在六千年前,伴随崧泽文化的浓浓乡音,鲜明独特的青浦田歌应运而生,不仅音乐结构丰富,而且凭借“多声部的合唱”让悠扬嘹亮的歌声充满了浓郁的质朴气息。
据说,到明清时,青浦田山歌就已蓬勃快速发展,每逢节气节庆,当地习俗流行对歌,隔河、隔田对唱,或者船头交锋,不失为水乡的靓丽风景。
现在,古镇朱家角也以“水乡音乐节”让现代人体验着仍然焕发活力的青浦田歌。
近年的“水乡音乐节”海报
上海不止有沪郊地区的民歌,在悠长的岁月里,郊区的农人与城市的工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谣。
此外,不止有以前传下来长歌,城市歌谣哼上几句便也有自己的感人肺腑,小市民口头传唱间就有各式各样的通俗唱本。
从前,有街头艺人的卖艺创作、歌女唱过的声声小调、工农劳作的唱作号子;现在,有代代传诵的耳濡目染,有《上海歌谣》里的“哭出嫁”、“城隍庙”、“龙华塔”等等的描绘,这块土地的生活样貌也更加具体。
别以为江南人士不习性直抒胸臆,田歌里的情爱也曾奔放热烈,《白六姐》《五姑娘》……听着彻彻底底的原生态嗓音,“无情未必真豪杰”,香糯柔软的吴歌方言里也有轰轰烈烈的爱憎分明。
汉语语言学、方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就曾说,最有情趣的民谣,当属情歌与儿歌,他曾回忆:
"跟着母亲咿咿呀呀地唱起那悠悠的童谣,似懂非懂地体会着那含意若明若暗的韵文,感受着母爱的温馨......母亲携着刚会走路的我,一边数着月影,一边又轻轻地念着:'月亮亮,家家小囡出来白相相。……'"
从这些短小平常而又意味隽永的童年顺口溜中,无数嗷嗷待哺和蹒跚学步的儿童第一次沐浴了上海民风的熏染,成为深入心底的乡愁记忆。
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些歌声被一代代上海人口口相传的并且,也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全新血液,它被“歌仙”陈歌辛谱成了一首首满载浓浓海派风情的乐章,被我们“克勒门”的掌门人陈钢记录成沪音传承间的全新经典,也被越来越多年轻的上海人用自己的方法重现着往日的感动。

雨天的上海,不妨和小克勒一起听一曲《上海谣》,回味一番“我家住上海,一代又一代”的感慨......
克勒门
是一个在上海
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的文化沙龙
如果你还不了解我们
就看看看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吧
点击以下文案直达
!
特别感谢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企业
静安区文旅局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原标题:《雨天秘话:“歌仙”的灵感来源竟然是......》
阅览原文
【主题】机会,这里是上海